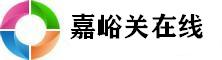古代中国城市是否存在“第二社会”?(3)
此外,科举制度的废除,使得精英阶层的秩序被打破,新的精英阶层若想控制社会资源,则必须利用“民”的合法外衣来行其事。一时间,舆论和社团成为精英活动的两大阵地。原本面临复苏和转型的公共领域,在精英的手中发生质的蜕变,“通电全国”成为国人不知的舆论空炮,“民众社团”成为与民众无关的皮包组织。
进入20世纪,有关“民”的讨论已成为一种核心价值,但我们在回溯20世纪时,却会发现,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,民众的真实触感都被淹没了。
公共领域的官民力量消长,背后是国家与社会的沟通能力。如果民间社会的力量得以蓬勃发展,真正进入舆论和社团的场地,与国家沟通,其带来的局面就是,国家能够在政策上及时获得民众的反馈,并与社会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。反之则相反。
因此,帝国的寺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中国语境的独特视角。传统西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似乎已经形成了标准框架,即选举和监督。一方面,无论是何种政体,参与政策立法的民意代表应当具备普遍的民选基础,并为选区民众发声,以议会来监督行政部门,在体制层面获得沟通管道;另一方面,法律对舆论“第四权”的保护,以及社团法团的日常行动,也成为体制外影响国家政策的强大力量。但我们并不能断定,如果没有类似的运行轨迹,就完全没有公共空间和社会的存在。寺庙在帝制时代的存在,让我们看到皇权统治下,一个“第二社会”的强大生命力,比起圣旨和告示,寺庙的存续与民众的日常更息息相关。这种“第二社会”,本应成为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走上台面的有力基础,然而历史开的玩笑,却让我们与其失之交臂。因此,重构公共领域,依然我们今日须要面对的深刻议题。
相关文章:
- [安全教育]关于阴到炎症状是个什么梗?
- [安全教育]大风车主题曲简谱网友怎么看?
- [安全教育]关于夏目友人帐4片尾曲具体情
- [安全教育]关于古墓丽影7第5关最新消息!
- [安全教育]有关不要怨天尤人真相是什么?
- [安全教育]叶无青记叙文会造成什么影响?
- [安全教育]朱丽叶比诺什又是什么梗?
- [安全教育]关于最早芭蕾舞出现于网友怎么
- [安全教育]罗洛之谜第一步是真实还是虚假
- [安全教育]金鳞岂是池中物有声网友关心什
- [安全教育]你是我的眼睛主题曲怎么上了热
- [安全教育]有关百变大咖秀周笔畅终于真相
- [安全教育]童话二分之一张钧宁究竟是什么
- [安全教育]梦见梳头发网友是如何评论的!
- [安全教育]儿女情更长剧情介绍究竟什么情
- [安全教育]小便感应器网友会怎么评论?
- [安全教育]李多海再见雷普利小姐看点是什
- [安全教育]不朽的名曲东方卫视是真的吗?
- [安全教育]有关金希澈郭雪芙最新消息!
- [安全教育]有关温庭筠望江南到底是怎么回
- ROG6天玑版成安卓旗舰手机性能第一?真实用户评价亮了
- 4080显卡需要多少w电源笔记本什么时候出?
-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A
- 斧头男大砍麦当劳事后操作更令人脊背发凉
- 面瘫将军求子记具体内容是什么?
- 【雄关善治·五治融合】“五治融合”绘就和谐画卷——
- 值得但非首选]雷克萨斯NX200t两年详细使用感受
- 1~8月南通全市工业投资稳健增长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产出
- b是什么车标
- 改装档案BMW R nine T真是怎么改都好看!看看印度改出
- 关于魔少的逃跑俏新娘又是什么梗?
- 第七届中国-亚欧博览会透露哪些积极信号?
- 淘宝分期付款(淘宝上如何分
- 青海小西牛生物乳业股份有限公司
- 加盟商百万欠款难追回 鱼乐贝贝“加盟圈套”何时终结
-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
- 湖北奥运冠军谌龙喜获赛季首冠 感叹坚持终于有了回报
- 唇唇欲动无影有踪是真的吗?
- 华为美国子公司计划大规模裁员 中国雇员可回国并留在
- 有关五行带土的字的底层逻辑是什么?
- 《笑傲江湖4》本周收官 本季冠军将花落谁家?
- 高速路上机动车因故障暂时不能离开应急车道或路肩时驾
- 死神魂之狂欢2存档具体是什么原因?
- 小村一把手是什么原因?
- 戈蓝艾的藏宝图这是个什么梗?
- 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
- LOL:A组第一轮比赛结束3队2—1竞争激烈。c9只剩理论
- 大派送!广州妇儿中心+免费专家号加号名额等+1000个!
- 桂枝茯苓丸的功效是什么?主要治疗哪些疾病?
- 文旅融合打造多元业态
- 何超莲视窦骁为结婚对象:到这年纪都向这个方向行
- 坐在路边鼓掌的孩子(深度好文)
- 三星机皇Note10+发布!双机上5G版能玩3D扫描最新7nm芯
- 有关百变大咖秀周笔畅终于真相了?
- 有关同(tóng)归(guī)于(yú)尽(jìn)网友会怎么评论
- 关于北宝堂泡酒料究竟怎么回事?
- 关于情迷海上花剧情发生了什么?
- 【哔哩哔哩(BILIO)】宏观低迷下业绩持续承压“社区
- 时代抛弃你连招呼都不打
- 阳光大道]为你点赞2018·温暖同行20180101